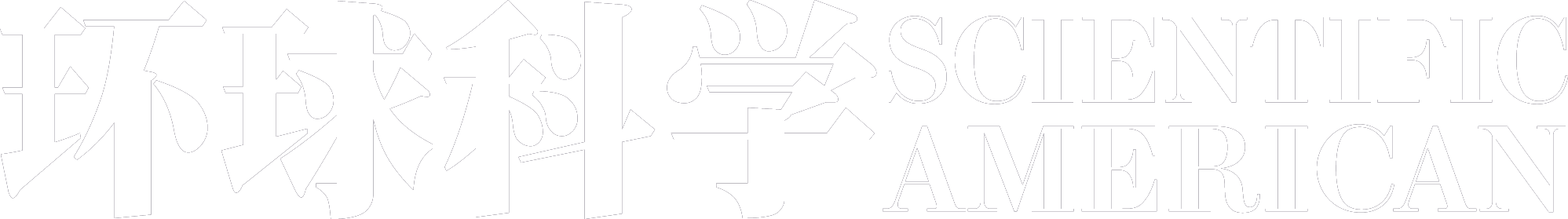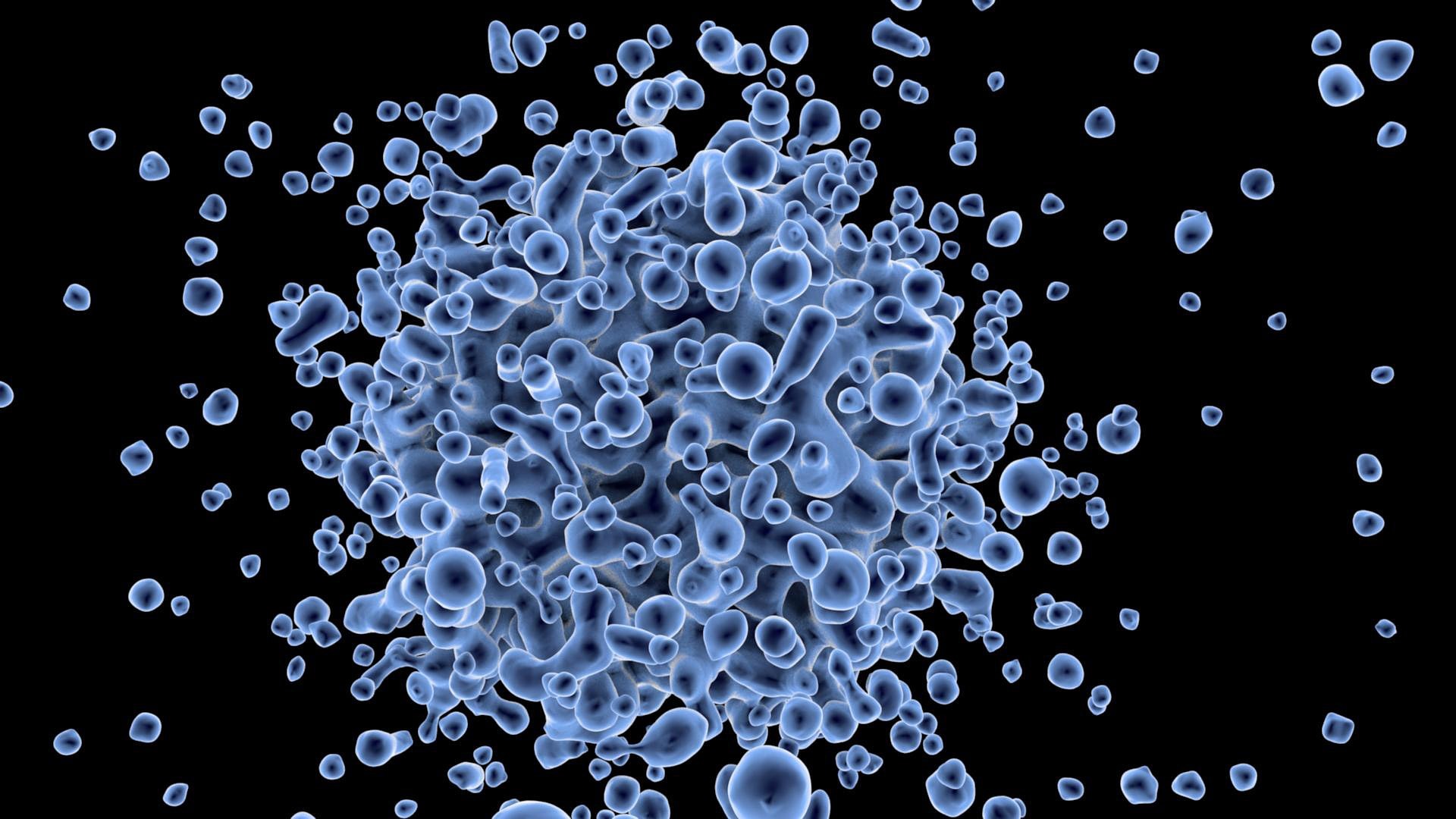
撰文 | 许伟凡(前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博士后研究员,目前是一家基于相分离技术的生物公司ByPhase Bio的创始人)
审校 | 李丕龙(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相分离现象的调控机制以及相分离相关技术的开发与应用)
编辑 | 黄雨佳
你或许还记得曾席卷全球的“冰桶挑战”。这场风潮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一群饱受折磨的患者。他们患有一种名为肌萎缩侧索硬化(ALS,俗称“渐冻症”)的罕见疾病,患者的运动神经元逐渐退化、死亡,肌肉逐渐失去功能,犹如身体被逐渐冻结一般,直至生命终结。然而,多年来,这种疾病的真正发病机制一直是生命科学中一个难解的谜题。
研究人员曾长期困惑于ALS患者脑中广泛出现的异常蛋白质团块,尤其是一种名为TDP-43的蛋白。过去很长时间内,科学家认为这些蛋白团块可能只是神经退化过程的副产品,而非疾病的根源。但最新的研究却逐渐改变了人们的想法:研究发现,这些蛋白团块的形成竟然可能源自一种全新的生物学机制——“液-液相分离”(Liquid-liquid phase separation,LLPS)。
什么是液-液相分离呢?想象一下,将几滴油滴入水中,油滴便会迅速融合,形成独立的液滴。这种现象也会出现在细胞内部:蛋白质和RNA等生物大分子在特定条件下,会自发地通过弱而多价的相互作用,形成液态的、动态的生物分子凝聚体(biomolecular condensates)。这些凝聚体并不被膜结构包裹,能自由流动、融合,发挥特定的生物功能。然而,这种本该高度可控的“液滴”一旦失控,凝聚体便会转变为不溶性的、固态的蛋白团块,毒性大增。这正是包括ALS在内的多种神经系统变性疾病的核心病理特征之一。
相分离的发现,第一次让科学家意识到,这些蛋白团块的出现并非偶然,而可能是细胞正常生理机制的异常偏离。这一新颖的分子视角彻底改变了人们对神经系统变性疾病病理机制的理解,也激发了科学界对相分离的极大兴趣。
诞生与兴起
事实上,生物相分离这一概念的提出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了长时间的探索和积累。尽管这一现象早在细胞中便有所出现,但直到十余年前,它才真正被生命科学界明确地捕捉并加以研究。
2009年,克利夫·P.布朗温(Clifford P. Brangwynne)和安东尼·A.海曼(Anthony A. Hyman)在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分子细胞生物学与遗传学研究所(MPI-CBG)合作,首次将物理化学中的“液-液相分离”现象引入生物学领域。他们在《科学》(Science)上发表了开创性研究,清晰地展示了秀丽隐杆线虫胚胎中的“P颗粒”并非传统的膜包裹细胞器,而是类似液滴的无膜结构,可以快速融合、自由滴落并动态润湿细胞内环境。这一惊人的发现首次打开了生物相分离研究的大门,也彻底刷新了细胞生物学的传统观念。
此后,大量研究迅速跟进,揭示细胞内部远比传统认识更为复杂。科学家们逐渐意识到,细胞实际上是由大量动态凝聚体通过相分离形成的复杂网络。例如,史蒂夫·麦克奈特(Steve McKnight)教授团队在《细胞》(Cell)等期刊发表研究,阐明蛋白质低复杂度序列结构域在相分离中的关键作用;德克·格利希(Dirk Görlich)团队则在核孔复合体中首次证实FG重复序列蛋白能通过相分离形成天然的核孔屏障。这些研究成果相互补充,推动了领域快速发展和成熟。
这些开创性的研究成果逐步揭开了细胞内微观世界的神秘面纱,使科学界逐渐认识到,细胞不仅仅是由膜结构构成的简单体系,实际上是一个由液态凝聚体和动态相分离组成的复杂网络。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科学家也积极参与其中,做出了许多重要贡献,逐渐形成了国际上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研究团队。例如,2012年时任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UTSW)迈克尔·罗森(Michael Rosen)教授实验室博士后的李丕龙首次在体外纯蛋白体系中完整重现了相分离过程,并明确揭示“多价态生物分子间的相互作用”是相分离的核心机制。这项发表于《自然》(Nature)的研究不仅奠定了相分离分子机制的理论基础,也为全球科研热潮注入了新的动力。
李丕龙并未停留在基础理论层面,而是进一步开拓相分离在医药和细胞信号调控领域的应用探索,逐步推动相分离理论向产业界转化迈进,成为中国科学界在这一前沿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
从“受体小镇”到信号调控
在一次跨越北美的长途航班上,李丕龙凝望着机窗外的夜色,茫茫黑暗中偶尔闪现大地上散落着的一个个小镇,发出一簇簇聚集的灯光。凝视着这些微光点缀的聚落,他突然意识到:细胞膜上的信号受体是否也会如同地面上这些灯光一样,自发聚集形成局部区域,以便更高效、更精准地传递信号呢?
带着这个灵感回到实验室后,李丕龙与团队开始了一系列探索。他们化身“分子建筑师”,创造性地设计出一类特殊的多价互作蛋白,能够同时抓住多个相同或不同种类的膜受体,将它们精准地拉拢、聚集在细胞膜的局部区域,形成稳定而有序的受体富集区。他将这种奇妙的膜结构形象地称作“受体小镇”(Receptor Town)。
在“受体小镇”中,由相分离形成的高密度受体聚集区犹如繁忙的城镇中心,让信号分子之间的沟通与协作变得更加快捷、高效。细胞不再需要漫无目的地等待信号分子随机相遇,而是可以通过精准的空间布局主动调控信号强度与精确度。这种巧妙的设计理念不仅帮助科学家更好地理解了细胞膜信号传导背后的分子奥秘,更进一步为生物医药领域的创新应用打开了崭新的大门。
“受体小镇”不仅在细胞生物学领域取得了基础理论上的重大突破,更重要的是,它为医药产业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天地。
传统的药物开发方式中,探索细胞膜受体的全新组合靶点往往十分困难。研究人员通常需要搭建庞大的抗体筛选库进行大量的实验筛选,不仅成本高昂、周期漫长,效率也十分低下。同时,这种方法在细胞膜受体组合的精准控制和信号强度的调节方面也极为受限,因此科学家难以发现真正具有高效药物潜力的受体新组合。
而借助“受体小镇”这一创新理论及相分离技术平台,这些长期困扰科学家的行业难题有望得到解决。通过设计特定的多价互作蛋白,科学家可以精准地将细胞膜上的特定受体高效、有序地聚集在膜表面的微观区域。这种相分离驱动的精准聚集方式不仅大幅提高了受体组合局部的浓度和信号强度,更显著增强了靶点组合筛选的灵敏度,让研究人员得以更快速、更高效地筛选出此前难以检测的新型膜受体组合靶点。此外,大量研究证据表明,相分离本身便是细胞膜信号传导的一种天然机制,因此,“受体小镇”的设计不仅是一项创新技术,更是顺应了细胞天然的信号传导规律,使其具备极高的生物相容性。
如今,基于相分离原理设计的“受体小镇”,已经开始推动癌症治疗等领域的疗法创新。例如,李丕龙实验室设计出的多价蛋白,能够在人为操控下,精准地在肿瘤细胞膜上构建功能明确的“受体小镇”。通过这种相分离驱动的膜结构,科学家可以精确且特异地激活肿瘤细胞内源性的死亡信号通路,诱导肿瘤细胞启动自身的程序性死亡,从而实现精准、高效且安全的癌症治疗新策略。
此外,利用相似的设计理念,研究人员也正在尝试构建聚集免疫检查点受体的“受体小镇”,以此来激活人体自身免疫系统对癌细胞的精准攻击,从而开发下一代免疫疗法。在神经系统变性疾病领域,通过精准操控相分离机制,科学家也逐步实现了对致病蛋白聚集过程的有效干预,有望研发出突破性的药物治疗策略。
可以说,相分离及其代表性的“受体小镇”不仅开启了细胞膜受体靶点组合探索的新范式,更有潜力彻底改变疾病治疗的传统模式,引领新一代精准药物开发的前沿趋势。
展望未来
从最初的实验室基础发现,到如今进入产业转化的快速通道,相分离领域短短十余年的发展已清晰地展现出一种全新的科学逻辑与应用前景。作为细胞内部精妙的分子组织方式,相分离不仅重塑了人们对细胞功能与疾病机制的理解,更首次提供了一种精准操控细胞膜受体与信号传导的新工具,从而开辟了药物研发中前所未有的靶点筛选和组合策略。
过去,医学界面对复杂疾病往往束手无策,很大程度上因为传统的药物开发模式过于局限于单个靶点的线性研究思路,难以处理更为复杂、精细的分子调控网络。相分离及“受体小镇”的提出与发展,使得我们首次能够从细胞本身的功能逻辑出发,通过精准构建膜受体的空间组合,快速、高效地发掘出此前难以识别的新型药物靶点组合。这不仅为癌症、神经系统变性疾病及其他疑难杂症的精准治疗打开了全新的技术窗口,也逐渐演变为药物研发领域的又一重要技术突破。
相分离不仅是一种先进的研究工具,更可能代表着未来医学范式转变的关键节点。当我们越来越深入地理解这种细胞本身就存在的天然机制,逐步实现对其精准的人工操控时,我们将彻底重塑未来医疗技术的范式:从“被动治疗”走向“主动精准调控”,从“症状缓解”走向“病理机制精确干预”。
展望未来,随着基础研究与产业化应用的进一步深入融合,相分离不仅将持续推动生命科学领域的深刻变革,更将在医学产业实践中逐步展现强大的实际价值。这一领域的未来远非遥不可及,而是真实而迫切地等待我们共同开启。